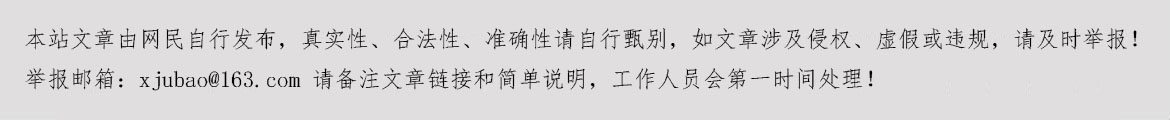大家好,我是陈拙。
你们可能不知道,父母很多管教我们的方式,放在国外算是违法犯罪。
前段时间有条新闻,一名华裔爸爸被老师举报虐童,一下罚了30万日元,还留下了犯罪记录。
这位父亲说,他只是因为孩子起床磨蹭,掐了孩子几下。
我的朋友侯小圣在海外多年,她告诉我,澳洲对儿童保护的法律监管更加严格。
比如,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单独在家超过一定时间;
也不允许擅自对14岁以下的孩子拍照;
吼骂孩子、打孩子算明确家暴,可能涉嫌违法。
当学到这些法律的时候,侯小圣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国内见过的一件真事儿:
一个妈妈跟踪了女儿19年,这算违法吗?
我留学澳洲的第四年,被外派到了一所残疾人学校当司法社工。
这是一所安静的学校,走廊上不常听见孩子们追打笑闹的声音,只有轮椅骨碌碌地走过。他们的世界就被圈在这里。
在这里,唯一喧闹的是一个中国家长。
在我还没来学校的时候,就曾经听过她的大名。
我的同事在午间八卦时说,自己接到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电话,自称她的孩子在残疾人学校,要求我们派一个社工专门照顾她的女儿。
接电话的同事解释,我们是司法社工,通常只服务涉嫌违法犯罪的案子,她女儿是出了什么问题吗?
没想到这句话惹怒了她,大骂同事没安好心,接着又说:“我是中国人!到澳洲凭自己本事找到工作,为澳洲做出了贡献,你们必须给我想办法!”
同事气得不行,复述这一段的时候说“中国人怎么了,中国人了不起吗?”我尴尬得不行。
本来不是自己的案子我不该看,但那天我偷偷找到了这个中国女人的名字,预备下次要是我接到她电话,就劝她别给中国人丢人。
当我来到学校两周后,我主动给这个中国家长打了电话。我说,你的女儿在学校向我求助了,我需要和你聊聊。
我准备告诉她,中国妈妈管理孩子的那一套,在澳洲涉嫌违法了。作为司法社工,我可以申请剥夺她的抚养权。
那天,有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了我办公室门口,堵我。
她不敢进来,我又没发现她,结果一出门把她撞了一下。普通人只要退一步就能站住,但那个女孩像不倒翁似地小幅度转圈,似乎下肢有残疾。
我赶紧伸手扶她,女孩攥着我的胳膊,支支吾吾地问:“你是新来的社工吗?你是中国人吗?”
我点点头,她攥着我的手一紧,说出了一句中文:“姐姐,你救救我,我被鬼缠上了。”
女孩名叫温馨,今年16岁,是这所残疾学校高年级的学生。
大概半年前,温馨曾向当时的驻校社工反映,有一个鬼白天黑夜都跟着她,但除此以外没什么特殊行为。
我的上一任社工推断,这应该是温馨幻想出来的朋友。她标注:“没有影响正常生活,也没有对他人构成威胁或者伤害。”
青春期的小孩确实容易受到刺激,或因为某种长期的压力而产生幻觉。但我却觉得不对劲,如果只是朋友,温馨为什么要说“救救我”?
我把她带回了办公室,小心地问她,这个“鬼”是什么样子的,会对她做什么?知道这些,我才可能推断出,是什么让她怕到产生幻觉。
她说,这个“鬼”会和她交流。
有时候,“鬼”会突然指挥温馨从教室里走出去,或者禁止她吃午饭,凌晨睡觉的时候会把她叫醒,告诉她今天不能再睡了。
“鬼”还威胁她,不听话会发生可怕的事儿,所以她从来不敢违背“鬼”的命令。
我警觉了起来——万一哪天这个“鬼”喊温馨去跳楼,该怎么办?
我先安抚温馨回去上课,转头联系了学校的前任社工。为什么她会给这个案例标注“不构成威胁”,是有什么情况我不知道?
视频电话一接通,一个响亮的女性声音就传了过来,前任社工贝蒂感谢我前来接班。
我说起温馨,贝蒂大笑起来,让我别那么紧张,特殊学校的学生因为生理残疾,心理和智力都会受影响,平时说话就是神神叨叨的,不能全信。
我皱了皱眉刚要说什么,贝蒂突然问我,你见过温馨的妈妈吗,那可是全年级“最难缠”的家长。
我这才知道,温馨的妈妈玛丽,就是我一直找机会想见见的那个中国家长。
贝蒂第一次见到她那天,是残疾人学校每学期一次的家长开放日,这向来是学校难得的喜庆日子,家长搂着孩子感谢老师,老师向家长夸奖孩子,其乐融融。
但温馨妈妈不一样,她参观教室的时候,突然一把掀开了桌板,要检查温馨的书包。
在我们看来,孩子的书包是个人隐私。更何况课桌是一条长桌,所有孩子的私人用品都放在一起,温馨妈妈这一掀,其他家长都傻眼了。
班主任找来贝蒂劝阻温馨妈妈,温馨妈妈说,她就是想看看,女儿有没有在学校好好学习。
好几个家长要求温馨妈妈向他们的孩子道歉,她反问:“我管自己的孩子,为什么道歉?”
作为社工的贝蒂紧张了起来,妈妈对检查孩子书包这事过于理所当然,有对孩子控制过强的嫌疑。
以澳洲的法律看,这属于家暴的一种。
贝蒂找温馨妈妈聊了聊,问她是否需要参与一些如何处理亲子关系的培训。结果温馨妈妈直接破口大骂,说你才有病。
她投诉了贝蒂,理由是对她人身攻击。
她还给副校长邮箱写了封举报信,措辞激动,要求学校严查她,“可能存在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”。
这顶帽子扣下来,贝蒂完全有可能被停职。怪不得她只想把温馨的事儿大事化小。
但我隐隐觉得,“鬼”就是温馨的妈妈。
第二次把温馨找来谈话,我有意识地问她,这个鬼是男是女?
但温馨含糊其辞,说不知道鬼是男是女,她没有正面见过这个鬼,鬼只会从背后拽她。
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对我还有戒心,但没有温馨的举报,我没法帮她。我得先跟她套套近乎。
温馨的资料中,兴趣爱好是去漫展,我跟她说,我也喜欢看动画片、买周边,在国内也常去看漫展。
温馨的眼睛一下亮了。她抓着我问国内的漫展,又滔滔不绝地讲起她最喜欢的《JOJO的奇妙冒险》。
我大概知道中国家长的问题,所以问她,妈妈喜欢这个漫画吗?
温馨的笑容一下僵硬了,小声说,妈妈禁止她看漫画,“妈妈说,温馨,你已经够没用的了,为什么还要看没用的小人书?”
像极了很多中国孩子,温馨最常从母亲那得到的评价是“没用”,她先天残疾的双脚就是没用的最大证明。她在轮椅上挂的小铃铛、给拐杖做的小装饰,都是“没用”的。
她很想穿成漫画人物的样子,但只能偷偷自制那些衣服。
她没钱买布料,就去学校的旧衣服回收箱偷。怕妈妈翻书包,温馨就把旧衣服穿在外套里面,一次带一件。
可她在服装设计上居然很有天赋,有人看到她发在网上的照片,专门请她帮忙做衣服。当她们穿着温馨做的衣服去漫展的时候,这个小裁缝连家门都不能出。
她16岁了,除了去学校,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妈妈的视线,甚至不曾自己去过家门口的超市。
在又一次提出自己出门被拒后,温馨突然倔劲儿上来了,拄着拐就往外冲。
她妈妈看着她一步一步挪到门口,在身后说,你出去了就别回来。
温馨没吭声,继续往前走,还没走下门口的楼梯,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咔两声反锁的声音。
温馨回过头,妈妈站在窗前,母女二人隔着玻璃对视。温馨知道,妈妈是永远不会向她妥协的,但这次,她也不想妥协。
那天,温馨在冰凉的水泥楼梯上坐了四五个小时,最终被邻居送回了家。
邻居警告温馨妈妈这是家暴,她才开门把温馨拉进来。
送走邻居后,她立刻转头对温馨说,你不要以为澳洲法律有多厉害,也别以为报警就真的会有效果,我是你妈妈,我对你有监护权,我想怎么管你就怎么管你。
我感受到了那一刻温馨的感觉,羞耻、困惑,甚至是对自己的亲生妈妈的恐惧和愤怒。
因为我也曾是这样。
我还在东北的时候,上小学英语补习班,老师在念单词听写,我紧张地咬手,窗外突然传来妈妈的声音:“不许咬手!”
那声音像打雷一样,老师被吓了一跳,盯着我说:“谁家长这么没素质?”
边上的同学问我,是不是我妈妈。我恨不得自己能消失在教室里。
我的妈妈,就像温馨的妈妈那样,总是想掌控我的一切。
小时候的我和妈妈
从小到大,我一直生活在妈妈的眼皮子底下。高中时,有一次同学邀请我去KTV参加生日派对,我很想去,借了同学的手机给妈妈发短信申请。
妈妈没有回复,我抱着侥幸心理去了,但不到八点,同学就接到了一通充斥着咒骂与吼叫的电话。她被骂了半天,才明白过来那是我妈妈。
同学把电话递给我,比着口型说:“你妈妈。”她说:“要不你先回家?”
她脸上的同情刺痛了我。
我躲到走廊最远的那一侧,只剩我一个人面对那个电话,全身都在发抖。
妈妈在话筒那边近乎破音:我在问你话!你哑巴了!为什么放学没回家不和我说!
我说我发过短信了。
“那我回了吗?我不回就是不同意!不同意你就敢去!你现在就敢这样,以后肯定是要犯罪的,要去杀人!”
妈妈是她那个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,骂人从不带脏话,擅长的是把一件事极端夸大,让你觉得自己不听她的话明天就会堕落,会去杀人,会成为社会的渣滓没有任何人爱你。
她可以从任何一件事开始,一句接一句,滔滔不绝地骂下去,让你来不及思考和反驳,只能被一个巨大的漩涡往下卷。
后来我读了社工专业,才知道妈妈对我已经达到了家庭暴力的级别,不止是语言暴力,她的控制欲就是病态的。
如果有一个司法社工强硬介入,甚至可以剥夺她的抚养权。
我同时也明白,妈妈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同样需要接受介入和治疗。
可是我知道得太晚了,对我们俩的一切伤害都已经不可挽回。
大三的时候我去一家英语教培机构实习,爸爸提出带我去逛街,我喜欢上一件绿色的短呢子大衣,带着一排羊角扣,是流行的款式。
我至今记得它的价格,499。
那一天,不知道为什么,妈妈竟然没有对我买这件衣服产生异议。
我捧着那个纸袋子,好像捧着宝物,回家之后穿上大衣,在镜子前左看右看,直到睡觉才脱下来,再小心地叠好,放回袋子,准备正式上班的第一天穿。
妈妈就在这时候突然变卦。
她先嘟囔了两句“这衣服还是有点贵”,很快就像我熟悉的那样,急促又大声地训起我来。
她先是讲道理,说工作能力跟穿衣服好看不好看完全无关,我根本不该去买衣服,以实习的名义要新衣服就是臭美。
接着她又说,现在就买500块钱的衣服,这是给我惯坏了。
最后她大声地冲我吼,你不配,你就不配穿这么贵的衣服!
我在她的吼声里闭上眼睛,不断地恳求,我累了,我只想睡觉,妈妈可以歇会再骂我吗?
可是她就是不停,就是不停不停地骂。
我深深地记住了那件衣服的价格,我记住了,自己配不上喜欢500块钱以上的东西。
以至于我第一次被表白的时候,男孩说完了话,满眼期待地看着我时,我犹豫了又犹豫,捏着拳头,最后脱口而出:“凭什么?”
凭什么你可以这样大方地说出自己的喜欢?
对于“离开家”这件事,我比温馨计划得更久。
高考报志愿,班主任按例要和同学沟通。我告诉他,我想去离家最远的地方,想尝试独立生活,想知道没有妈妈监控的人生是什么样的。
班主任听完,重重地叹气,说他理解。
我再三要求他,保证不会告诉我家长,他让我放心。
可是到了报志愿那天,妈妈直接给了我一份填好的志愿表,是一所本地的大学,近到每周都能回一次家。
那天,她格外温言细语:“妈妈问过你班主任,他说你想去广州读大学,那太远了,你去那么远不会适应的,是不是?”
我只觉得绝望。
那时候我特别怨恨班主任,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帮我,今天我明白了,对他而言,我只是一个家长特别难缠的小孩,应付好我的家长就可以了。
可是他不知道,他的纵容把我推回了一个什么地方。
高考结束后,我还是去了那所本地的大学。
我不能离开学校,不能离开妈妈的视线。她要求我每周回家,还会莫名其妙地突然跑到我的大学,只为了看我有没有“好好表现”。
我的课程表她比我还倒背如流,如果我没课又不在寝室,就马上会接到无数个电话,无论我怎么解释,妈妈都会一口咬定我偷溜出学校,去玩了。
我曾经尝试把电话放在一边置之不理,结果,妈妈带上姥姥和小姨一起到学校找我。
不知实情的姥姥急得满头大汗,问我为什么要气妈妈,你怎么上了大学连妈妈电话都不接了?
妈妈甚至已经替我计划下一步的人生,我要考上本校的研,再去考公务员,接着相亲、结婚。她“宽宏大量”,允许我“第一年考研失败”,但第二年必须成功。
这个计划里,她没有打算打我、把我卖掉、杀掉,可是实际上,我每一天去哪里、买什么、和谁说话,都可能被妈妈视为违规,都会招来几个小时的斥骂。
我仍然每天都要紧绷神经思考怎样才能不挨骂,而现在,我还要用晚上来做噩梦,我总是梦见我已经长到妈妈的年纪,她还坐在我床边冲我大吼,你今天要去哪?你怎么不和我说?
我抓着身边所有同学问,问他们毕业之后打算去哪,我想知道除了高考还有什么离开家的方式。
有个好朋友说,她打算去英国读研,问我要不要试试申请?
这句话让我突然看到了一条新的路。
我查了英国距离中国的距离,不到八千公里,飞机不到12个小时。
那时候我对签证没有概念,只觉得这个时间还是短,如果妈妈某一天突然要来找我,一夜过去她就会站在我面前。
我继续搜,距离中国一万公里的国家有哪些?
澳大利亚跳出来,我立刻就认定了它。
后来所有人都很难猜到,我留学、学社工,看起来乐于助人、对世界充满爱,但这一切的开头,只是因为我不顾一切地想要逃跑。
我偷偷计划着考雅思。
雅思考试一般在周六,我报名参加了学校唯一一个周六有活动的社团,把活动通知发给妈妈,又嘱咐朋友替我去参加活动,如果看见我妈来了,尽量帮我拖延一下。
那天下午,我考完口语,急急忙忙地打车回学校,冲进了校门——
电话没有响起,妈妈没有发现我这一次小小的出走,我像劫后余生一样心脏狂跳,又不停地笑。
我终于离开了她。
近五年后,我在澳洲仿佛又见到了我妈妈。一个陌生女人脸上的神情,和她非常像。
那是温馨的妈妈玛丽,她坐在我对面,留着乌黑整齐的短发,穿着一整套西装套裙,搭配墨镜、耳环和一个小包,看起来不像是来谈话的,像是来找我谈判的。
她来回打量我,我迎着她的目光挺直了背。从我的背后,大窗户外的阳光不断地传来热量,这是我的办公室,是我的地盘。
我平静、专业地向她自我介绍,然后告诉她,我得知温馨可能被勒索了。
玛丽脸上露出一个我极其熟悉的表情,这表情我曾在自己的妈妈脸上见过无数次,不屑,轻蔑,又不耐烦。
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个不受控的声音,这声音越来越大,近乎咆哮——
她说,求求你别问温馨怎么会有钱,求求你先关心自己的孩子,她已经是受害者了。
但玛丽一张开嘴,就像设定好了一样,说:“胡说八道,温馨哪来的钱?”
我曾以为我早就离开了家,离开了名为母爱的怀疑,控制与打压。我以为我已经走得够远了,在距离家乡一万公里外的地方,我不会再觉得痛苦了。
但这一瞬间我意识到,我所经历的那种连绵不断的痛苦,正在不停地重演,有那么多父母不知道怎么去爱,只知道以爱为名的控制。
我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个个抛给问玛丽:你有没有想过,孩子被勒索了,找过学校社工,找过我,甚至想过就这么算了,但为什么没有想过去找你帮她?
她愣在那里。
我抱出温馨的档案,问她,你有翻温馨书包的习惯吧?你想知道温馨在学校里都发生了什么,让我来告诉你。
那天,我和温馨聊了很久漫展、COS之后,我再问了她一次,那个“鬼”到底会对她做什么?
她迟疑了一下,终于坦白告诉我,“鬼”会拿走她书包里的钱。
温馨把做衣服的收入都藏在学校,一部分放在书包里,一部分放在书桌里。两个同学无意中发现了她有很多现金,说要汇报给班主任。
温馨恳求她们,一旦告诉班主任,她家长势必会知道,到时候事情就大了。
或许同学们一开始是在开玩笑,说那你给我们一人五块钱,我们就不说。
温馨毫不犹豫地给了。
她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,想不到很快有更多同学知道了这件事,纷纷找她要“封口费”。
他们都从自己的家长嘴里听过温馨妈妈的事迹,知道温馨最怕的就是“让你妈妈知道”这六个字。
温馨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同学们停止勒索她,又不敢如实地告诉班主任,于是,她自己编造了一个“鬼”的故事,希望引起社工的注意。
我把这些玛丽不知道的事一一告诉她,告诉她她女儿的勇敢、恐惧和爱。
她的第一反应是愤怒,伸手来抢档案。
我立刻警告她,如果她再乱动我就按紧急按钮,她会涉嫌违法。我也告诉她,她对温馨的语言暴力、人身自由控制,她侵犯温馨的个人隐私,可能已经触犯了种种法律。
我不是打算把她送去坐牢,而是想告诉她,这是非常不对的。
我在她的斥骂声中坚定地、一字一句地告诉她,我不会放任未成年人在家庭关系里受到侵害,你女儿最大的心结在你身上,你必须处理。
“如果你不能处理,可以接受怎么做妈妈的培训,如果你还是做不好,那就别再做妈妈了。”
在这片大陆上,法律远高于母亲的权威。
玛丽显然没有马上被说服,只是愤怒,但终于不敢对我做什么,站在原地急促地深呼吸,然后突然转身走了。
那之后是周末,我不知道她和温馨谈了什么。但周一,我收到了内网的消息,玛丽真的去参与亲子关系的培训了。
我看到了她的问答记录,她的回答也很像我的妈妈。
那份问答记录就像四年后的我终于可以不卑不亢地去问妈妈,你身上发生了什么?为什么这样“爱”我?
年轻时的妈妈是个大美人
玛丽是福清人,90年代来到墨尔本,因为英语不好,起初只能在餐馆打工,从每天早上十点干到晚上十点,一个小时八刀。
这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,是违法的,但她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这样是被压榨的。
她想要融入澳洲,她是她们家唯一一个选择了出国的,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深深地扎根下来,才能够配得上她付出的代价。
很快,玛丽和饭馆的一位常客熟了起来。
那是一个很友善的澳洲男人。因为英语不好,她经常上错菜,这个男人会替她解围,还会特意去找老板帮她说话,说觉得她是好员工。
玛丽觉得他人很好,鼓起勇气主动约他出去,直至走到结婚。
她毫不避讳地说,和丈夫结婚、拿下伴侣签证是她融入澳洲的一个门票,她觉得她的努力终于有了意义,新生活就要开始了。
但她向上攀登的人生计划,被一个双腿畸形的新生儿打破了。
丈夫安慰她说,这不是什么大问题,政府福利也有保障,温馨可以过得很好。
可是玛丽没法接受,她不明白自己设想得好好的新生活为什么出现了偏差,她觉得一切都完蛋了。
量表上有几个问题:
你是否觉得女儿把你的成功打断了?
是。
你是否觉得你对女儿的残疾负有责任?
是。
玛丽把这一切愤怒、委屈、抱歉,变成了对温馨无孔不入的控制。她禁止温馨自己出门,管理温馨的交友和喜好,她想要把一棵开始就长歪了的树扳回轨道。
可是她忘记了,孩子不是植物,他们生来就是要自由生长的。
咨询要结束了,按例我们该给她一个问卷,询问她对这些咨询是否满意。
因为知道这位女士有多挑剔、对自己的育儿理念有多固执,同事不敢把问卷链接发给她。但问卷收上来后,同事非常意外地看见,她写了满意。
温馨后来给我的学校邮箱发邮件,说她想要回国,去读国内的大专,成为专职裁缝,再去长白山看看。她喜欢《盗墓笔记》,长白山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。
隔一段时间,她就会写一封,说最近和妈妈聊了什么。最近一封邮件说,“妈妈带着我回国了,我们以后就在国内生活。”
我不知道,放弃在澳洲拼命夺来的一切,对玛丽来说是对是错。
两年前,因为疫情的原因,我也回了国。隔离一结束,我就去了墓地,去看妈妈。
我的妈妈,已经离世七年了。
是的,并不是因为考过了雅思,我就能顺利逃离,留学需要一大笔钱,我不可能在妈妈的管控下挣钱。是因为妈妈死了,我才得以逃出她的控制。
她被确诊肝癌那天,是个春天的下午,北方风沙漫天。
我那天在考试,没有带手机,走出考场才看见几个小时前她发来的消息。
我到家的时候,她罕见地没有大喊大叫,只是坐在沙发上发呆。我走过去坐下,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我觉得痛苦,因为我就要失去她了,我又觉得快意,因为我终于看到她被打败了一次。
我依旧觉得困惑,妈妈,你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态在爱我?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?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,我也不敢问。
最后我们谁都没有说话。
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某一天,回家路上看见的月亮
在她病到已经不能自主排泄的时候,她依旧把所有的力气用在我身上。
我下班回家带着一包麦当劳,她恶狠狠地骂我只会吃垃圾食品,但她的眼睛已经暗淡下去,也不能再借题发挥几个小时了。
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和她据理力争,或者听到她骂我就想哭,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,看到她闭嘴为止。
我也曾经试着跟她聊,问她为什么这样对我。
她一开始轻描淡写地说,那是为了让你不走歪路。
但我追问下去,她就会大喊说,你疯了,你就这么想妈妈的!
她停止呼吸那个早上,给我发了一条短信,要我照顾好自己和爸爸。
她在那条短信里叫我的小名,她说她爱我。
是吗?
我在此后的七八年里,常盯着这条短信出神,我为什么体会不到你的爱呢?为什么我从小到大,永远只觉得被控制、被打压、被监视?
她走之后很多年,我尝试登陆她的QQ号,在空间里看见了很多“仅自己可见”的日志。
我以为,我终于可以破解她为什么那样对我,比如,因为童年的不幸,因为婚姻生活的不顺,但没有。
六十几篇日志,每一个主题都是我,我长高了,我第一次月经,我高考那一天她有多紧张,我上大学第一天她有多不舍。
这一切只是加深了我的困惑和痛苦,我不明白为什么,她会把这样的爱表现为源源不断的指责?她在这样爱我的过程中,真的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痛苦、愤怒吗?
爱就是要让人痛苦,也让被爱的人痛苦吗?
我第一次降落在墨尔本机场那天,和玛丽的感受是一样的,我的新生活开始了。
我参加各种社工课程,同学们友好、包容、关心你的一切情绪。我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和案例,里面有很多痛苦,我也试着理解自己的痛苦。
我开始接受心理咨询,学习法律。
社工有很多种分类,也有很多种方法论,有的人会用心理学的方法帮助人,有的人用金融学、社会学。
而我喜欢法学,法律像一个坚硬的盾,保护底线,并且将这个底线越抬越高。
我开始试着做案例,帮助别人。
我没有忘记妈妈,我也没有和那种痛苦和解,可是我已经学会了一套新的“爱”,我不会再那样让别人痛苦了。
我尝试重新审视我和妈妈的关系,我不会说我已经和解了,但我能让自己不再被她影响。
我追究过去的伤害,不是为了报复造成伤害我的人,是为了让我能学会用“爱”的方式表达爱——而这件事,什么时候都不晚。
回国看妈妈那天,我带着一个辫子和五盒冰淇淋。
辫子是她化疗时剪下的。她留了很多年的长发,辫子乌黑亮丽,非常漂亮。我一直把它放在行李箱里,跟着我满世界跑。
冰淇淋则是四个蓝莓口味,和一个香草口味。她最喜欢蓝莓口味,临终前几天还指挥我给她买。
但她又最讨厌香草口味,我想她拿到了肯定要来梦里骂我,你买的什么东西,你妈喜欢吃什么你记不住,你这个脑子怎么长的?
但她一次都没有来过。
在刊发这个故事之前,我一直挺担心的,这会不会不好?会不会显得特别斤斤计较、恩将仇报?
毕竟,“那是妈妈呀”。
后来许多朋友告诉我,这个故事让他们想到了自己。
被妈妈翻看日记本和同学的聊天记录;每次出门都要经过母亲的许可;甚至连头发的长短都要受母亲的控制。这些经历都是很小的事,却让他们太难过了。
为此,我特意向社工侯小圣要到了一些具体的应对方法。如果你的父母同样控制欲很强,下面这些方法也许能帮到你:
1.不要和父母讲道理
对于控制欲强的父母来说,这是在挑战权威。
可以转移父母注意力,比如鼓励父母发展某种兴趣爱好,用求助的方式,请他们帮你打毛衣、做饭等等。
2.拉开物理距离
尽量通过考试、竞赛、找其他亲戚等途径合理地远离父母。不在家庭环境里,拒绝被父母控制也会比较容易。
3.寻求同辈支持
和一些能够安慰你的朋友交流,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情感支持,尤其是告诉自己“世界上仍然存在一种理想生活”。
4.为自己建立一个目标,并在这种特殊节点设置一场仪式
比如在高考后举办一场成人礼,或者夜不归宿,买一件想要很久的东西等等,向父母真正宣告自己的力量,从而争取谈判的筹码。
侯小圣希望,这些方法能帮到曾经或正在被父母伤害的孩子们。
当然,她更希望,母子间自始至终都不产生伤害,让这些方法永远不被用上。
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编辑:卡西尼 马修
插图:徐六耳
部分图片来源于作者